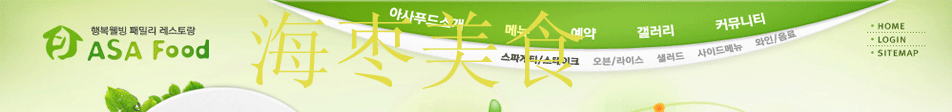|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前,地处大巴山南麓的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在城镇化、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方方面面,摸索出了“社区+工厂”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平利模式”,积极通过干部与贫困户结亲帮扶,补齐“短板”,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受到贫困户欢迎。 但平利县个别乡镇——大贵镇遭到当地群众举报:精准扶贫帮扶举措照猫画虎,“不精准”的一户一策只是纸上谈兵,干部玩典型经验“假报道扶贫”;扶贫户的“明白卡”(指精准扶贫结对帮扶明白卡)成驻村领导“遮羞卡”,贫困户家无镇领导踪迹,干部玩“纸上扶贫”;搬迁安置点无“工厂”、无“基地”配套,搬迁农民稳不住难致富;真正的特困户仍住深山危房等现象。 年10月16日,采访组一行4人,从北京出发,经过两小时自东向西的飞行,由高速路从北向南穿越过隧道无数的秦岭,再经近一个小时崎岖山路的颠簸摇晃,来到了安康市平利县大贵镇,进行了为期3天的明查暗访。 资料显示:大贵镇,位于平利县城西部,距县城25公里,距安康35公里。东与城关镇相连,南与洛河相依,西以三阳为界,北与老县为邻。总面积平方公里,1.4万人。大贵镇,源于成语大富大贵而得名。 采访组先后走访了嘉峪寺村、淑河村、柳林坝村等3村49户精准扶贫户、危房户,农民二哥对大贵镇党委政府的避灾移民搬迁和精准扶贫怨声载道。 距离镇政府不足一公里的嘉峪寺村,位居黄洋河两岸,地势宽阔,田野平坦,公路畅通。年后,中央号召走城镇化道路,部分有点积蓄的高山农二哥,响应号召,下决心“挪穷窝”到山下安置点或对口村组自建居住房。 嘉峪寺村知情村干部检举说:几十户“挪穷窝”农民没有想到村嘉峪寺党支部书记王文康有“土政策”,向搬迁户收取宅基地费每间0.5—2万元、建房占补平衡费—元、土管测设费元、人头费每人元,有的还收取公路占用费元、建房保证金0.5-1.7万元、拉电费、吃水费等,总计需要交2-8万元。 搬迁户孙明余、孙明勇、倪昌兵等人反映,农民本身积蓄少,交清村干部“土政策”规定的款项后,所剩无几。建房子的钱一方面向亲戚朋友借债,一方面向信用社贷款盖房。房子建起了,却负债累累,跌入了贫穷的万丈深渊里。他们还反映: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康收取这些不合理的费用时,都不给打“条子”(收款收据)。 搬迁农民赵大友、倪昌玲、袁启杰、李华山等反映,“挪穷窝”农民自建房2间2层楼房,盖房、装修等至少需要花销15万元以上;加上彩电、冰箱、洗衣机,沙发、衣柜、席梦思……等,至少需要20万元以上。 采访组到大贵镇嘉峪寺村、淑河村、柳林坝村三村安置点(含搬迁分散建房户)抽样调查百户农二哥搬迁花费情况,结果显示: ——搬迁进新房时,外债在15万元以上的占53%,外债在10万元以上的36%,外在在5万元以上的占9%,无外债的只有2户,占2%。 ——截止到年9月底,百户搬迁农户,还清外债的有21户,外债在5万元以上的有15户,10万元以上的有46户,15万元以上的还有16户。 ——还清外债的21户农二哥,3户为当地跑运输的,18户为外出打工的。外债15万元以上的16户农二哥,4户因为欠外债单方外出打工,一方有外遇,导致家庭破裂;7户在当地从事养殖业(鱼、猪、鸡),不善经营亏本又欠外债;3户开农家乐又带外债;1户为入股当地挖矿欠外债;1户为跑交通遇事故带外债。 采访中了解到,享受了移民搬迁补贴的搬迁户,都不能被列为“精准扶贫”户。 嘉峪寺村莲花组农民乔Y说,他们家的水田和旱地总计8亩多,一次性被村委会以每年支付租金元/亩,强行以租代征的形式卖给砖厂挖土烧砖30年,没有给他家留下一厘土地,他家蔬菜都无处种,家里3人就靠外出打工挣钱糊口。 乔Y说,他们家3人8亩多农田租金一年一支付,每年总共元钱,平均每月才元,平均每人元;靠这点钱仅仅够买点粮食,无钱买蔬菜了;失去了土地,这是他们家越来越穷的主要原因。 乔Y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打工了,砖厂已经把他家农田挖没有了,也无法给恢复了,以后无法生活了,他们家是最困难的贫困户。目前,镇、村干部对他们家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调查发现,嘉峪寺村莲花组像乔Y这样,农田全部被村委会强行流转给砖厂烧砖的有4户,流转一部分农田的有10多户。 按照精准扶贫的原则,4户失地而又离开土地又无法生存的农二哥,应该调节出一份土地,发展生产致富;至少应该调整出一块菜地,来解决农二哥“菜篮子”问题。 采访组询问,村组集体是不是没有土地可以调整了?乔Y回答说,村集体和组集体还有12亩基本农田,被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康强行霸占建成沙厂,挖沙卖沙已经成为千万富翁,那里还顾得上咱失地农民的死活! 嘉峪寺村知情村干部证实了农民老Y的说法,他说:嘉峪寺庙倒塌后留下一部分土地、村小学撤并后的校园地,约有30多亩都归村集体所有;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康私自把这些土地,流转到自己儿子王鑫名下,12亩划归给他儿子退耕还林,中途又私自全部卖给砖厂取土;他儿子一手拿着卖地款,一手拿着退耕还林补助款。 精准扶贫如何“精准”?从大贵镇政府对外的新闻报道看到,他们的经验是:全镇户个贫困人口按照“规划到户、措施到户、责任到人”进行精准帮扶。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分别实施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兜底扶贫等不同措施,制定出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脱贫路子,做到“一户一对策、一户一帮扶”。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知情人说,大贵镇联村领导、联村干部,到一些危房户、贫困户大门外墙上钉上“明白卡”牌,就万事大吉了;这些领导却没有到过这些贫困户、危房户,“明白卡”只是领导的“遮羞卡”。 走进淑河村中心组精准扶贫户今年70岁的张付国家,指着他家的“明白卡”询问:你认识你家的结对帮扶负责人-镇领导彭Y么?你认识镇党委书记陈S明么?陈S明书记和彭Y到过你家吗?回答:不认识,没有到过我家,也没有见过。 询问:你们家是精准扶贫户,镇干部、村干部都帮你干些啥?回答:给我订了个牌子(指明白卡),让下雨天防止破房子倒塌了。 采访组看到,张付国房屋外墙上的“明白卡”清楚地写道:年1月1日帮扶,帮扶前年人均收入元;年12月脱贫,脱贫后年人均纯收入元;脱贫措施:政府兜底。 “明白卡”让人看不明白:经过两年的扶贫,扶贫前人均纯收入和扶贫后人均纯收人相等,这叫什么扶贫?!扶贫前是危房,扶贫后依然是危房?! 接着又走访了淑河村花门组的贫困户王丛林和王丛良这2户,他们的情况与张付国家基本相同;精准扶贫“明白卡”上写的完全一样:年1月1日帮扶,帮扶前年人均收入元;年12月脱贫,脱贫后年人均纯收入元;脱贫措施:政府兜底。这两户扶贫户扶贫前是危房,扶贫后依然是危房?! 淑河四方组冯世兴大门上的“明白卡”清楚的写着:致贫原因是交通条件落后。这更让人不明白了——通村路就从冯世兴家院坝经过,怎么可以捏造因“交通不便”致贫呢?!那些离公路1公里或不通公路的贫困户,却为何不是因为“交通不便”致贫?! 随后又走访了淑河村樟树组沈大付、尧远林、尧风运、冯世福、余德刚、王武平等8户贫困户,询问:你认识你家的帮扶负责人-镇领导彭Y么?你认识镇党委书记陈S明么?陈S明书记和彭Y到过你家吗?回答都惊人的一致:不认识,没有到过我家,也没有见过。就连脱贫措施,回答的几乎都一样。 走进淑河村委会,全村贫困户分解图一目了然。村监委会主任陈永友介绍说,全村精准扶贫户户多人,年计划脱贫。 采访组询问:扶贫户为啥不知道自己“明白卡”上的扶贫措施?贫困户为啥不认识联户帮扶领导干部和帮扶干部? 大贵镇健康扶贫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攀登上柳林坝村垭坪组,这是大贵镇境内第二大高山。被撤销的垭坪小学就建在这个山垭上,一排长排摇摇欲坠的校舍呈现在眼前,依稀可以辨认出墙体标语模糊的字迹: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巩固农村教育阵地。 在垭坪远眺,杜甫《望岳》油然涌上心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同行的垭坪组农民柳意才介绍,现在还居住在垭坪组的至少还有11户,这11户有9户是贫困户;采访组走访了7户贫困户,其中4户为因病致贫—— 代召坤家的“明白卡”显示,他家结对帮扶的时间是年1跃1日,脱贫时间是年12跃31日,脱贫措施:医疗救助和技术培训。 代召坤家说,他母亲病入膏肓,没有人对他母亲进行救助,也没有人对他本人进行任何培训。 随后,采访组还走访了柳林坝村11户精准扶贫户:和平组的贾洪军、严贵富,花板组的王正军、肖兴寿,垭坪组的孙明周、杨波、孙自堂,金阳组的兰光义、陈进满、韩泽平,红池组的潘应贵。这11户的“一户一策”也只是“纸上画饼”,并没有实施。 调查发现,地处大巴山南麓深山区的淑河村、柳林坝村、杨家沟村,发展十分滞后,散布在山谷沟壑的土坯房,仍然是部分农民遮风避雨、安身立命的居所。 在淑河村、柳林坝村、杨家沟搬迁安置点了解到,搬迁户没有配套的菜地,吃菜需要购买,购买的蔬菜品种也十分单一;商贩贩卖的部分蔬菜是从百里外的安康城区运来的,价格比安康城区还高。这样,安置点农民的生活成本太高,生活质量下降;部分移民房屋转让给他人,有的回老家,有的出外漂泊打工;有的搬回老家住去了,把安置点当旅社,偶尔住住。 大贵镇政府一名领导指出,大贵镇前任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死死抓着陕南移民搬迁这个“集中安置”政策不放松,搞一刀切,忽视百姓生命安全;对“分散建房”、就地建房的不管是否合理,一律不允许;导致真正的贫困户、受灾户、危房户、五保户等特殊人群、特困群众搬不出。 位领导说,大贵镇现任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了突出政绩,眼睛只盯着建一、两个社区,只注重集中安置,不注重小集中或分散安置;只注重在交通要道建产业园区,不注重其他耕地的荒芜;只注重跟风产业建设,不注重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山林经济产业建设;只注重矿产品滥挖乱采,不注重保护青山绿水。 针对大贵镇的移民扶贫搬迁和精准扶贫问题,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建议,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和“富”都作为重点来抓。同时,对离开土地无法生存的贫困户、危房户,应该适宜小集中,比如一个田坝、一个村、或一个农民小组、或一个8户、10户的家族,建个小安居点;个别的村户,也可以适度分散建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