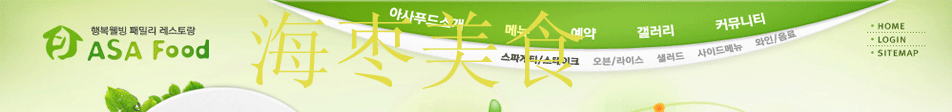|
孙鸿教授 孙鸿,陕西旬阳人,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安康学院首届教学名师,安康学院校训创作者。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任安康学院学术委员会,安康学院文传学院教学督导组组长中国散曲研究会会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主讲课程主讲《中国古代文学》(省级精品课程)、《诗经与楚辞专题研究》、《唐诗宋词专题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赏析》、《文艺心理学》、《影视美学》、《古代汉语》、《古代文论》、《艺术概论》等课程。 主要贡献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古典美学和安康地域文化。先后主持《中国古代文学》省级精品课程,主持或参与省厅级、市级社科基金项目6项;主持或参与院级、市级科研及教研项目10项。出版专著《中国古典美学气论研究》;主编或参编《陕西当代长篇小说研究》、《安康当代文学史》等安康地方文化论著及作品集20余部;在《小说评论》、《西北师大学报》、《名作欣赏》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发表论文《诗经》中安康文化元素的利用 《诗经》中的汉江是作为各种景物描写的对象出现的,是提示一定的地域特征的符号。作为地域符号,“汉”是与河、汝、江诸流域一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而在这个整体中,汉水充当了接合各个文化区域的作用。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许多诗篇都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余年的民歌与朝庙乐章首。“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周朝都城地区的作品,多由朝廷官吏所作,是周王朝的乐歌。“颂”是西周统治者用来作为祭祀的乐歌。“风”又称“十五国风”以民歌为主,它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风”所含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跨汉水与淮河,南接长江荆楚之地,其中《周南》、《召南》主要来源于当时的周国南地,即江汉流域。 《诗经》中与汉水流域相关的作品不仅仅体现在二《南》中如《周南·汉广》之类的诗中:“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也同时出现在《雅》中。《大雅·江汉》中便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诗句。由此可见,《诗经》的风、雅、颂中几乎都有诗篇与南国,即长江、汉水流域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就说明了汉水文化在《诗经》中是广泛地存在着的。 一、《诗经》中的安康 《周南》与《召南》所处地域的主体即汉水流域,这一点是无疑的。因此《周南》、《召南》在《诗经》中的地位也就很好地说明了汉水流域或者汉水文化在《诗经》中的位置。但要找寻《诗经》中的安康,却是一项较为巨大艰辛的工程。一则《诗经》既不是纪实文学集,更不是史籍,而是一部抒情诗歌集。诗篇中即便有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更何况,文学所传达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二则即便是《周南》、《召南》这些主要来源于当时的周国南地的诗歌,其中的诗篇出现的河流名不止汉江,有河、汝、江、汉等河流名称,可见,在《诗经》中,汉水是与上述诸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而安康又只占汉水流域的五分之一的区域,所以要在《诗经》中找寻关于安康的文化信息,实属不易。 当然,这也并非一件没有可能性的工作。在“十五国风”中,《周南》共11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河南省洛阳以南及江汉流域;《召南》共24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因此,我们不妨结合相关史料,参考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从二南尤其是《召南》的研究入手找寻汉水上游的文化信息,进而探知安康的文化信息。 此外,《周南》《召南》实际上是江汉流域民歌集,它说明长江、汉水流域民间歌谣的创作历史是久远的,它的流传、扩散及创造能量是巨大的。从《诗经》的首篇《关雎》的泛化情形,可以推测《诗经》在江汉流域生根普及的程度。《关雎》开篇四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汉水流域民歌有:“关关雎鸠一双鞋,在河之洲送过来,窈窕淑女难为你,君子好逑大不该,年年为哥来作鞋”的版本,以及“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的版本,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今流传的汉水民歌中进行追溯性研究,上溯到《诗经》时代,进而探寻《诗经》中的安康。 借《诗经》宣传安康首先是安康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资源已由一种软性资源变成了一种紧俏硬性战略资源。它一方面带来了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对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并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各地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热潮,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其次是安康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安康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就总体而言,外来文化(秦楚文化、巴蜀文化)的融汇大于其本土原生文化的影响,文化输入性因素大于文化输出性因素。因而,以《诗经》为切入点之一,在中华民族及各区域文化间的交融渗透的理念下探讨安康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挖掘安康文化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安康文化发展的重要步骤。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资源价值实现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旅游宣传及由此带来的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作为汉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汉水上游的汉中及中下游的河南、湖北而言,安康的历史文化积淀不够深厚,文化根基也不够深厚,因此,借《诗经》推介安康旅游,是为了给安康旅游宣传寻找一个自我宣传的历史文化依托,从而拓展旅游宣传思路,进而找寻安康旅游发展新的契机。 二、《诗经》中的安康文化元素利用 “汉水游女”出自《诗经·周南·汉广》,诗曰: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汉之泳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汉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汉之永矣,不可方思。 诗人在游春时节,来到汉水边,看见一位美貌女子,顿生爱慕之心,幻想着能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迎娶她,但无奈的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诗人一唱三叹,透露出爱而不能,可望而不可及的苦恼无奈之情。有些注家认为,诗中的女子是指汉水神女,游是指其飘行于水面之上。尽管在学术界支持率较高的是前一个观点,但是,汉水神女的形象已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据此,我认为如果要将“汉水游女”塑造成汉水文化“形象大使”,以第二个观点为依据进行策划则更有挖掘的空间,更有文章可做。如此,可以从古代文学中种种关于汉水神女的描写中,抽取或者提炼出她作为形象大使的元素。 如果将“汉水游女”搬上汉剧舞台,应以“汉水女神”为切入点进行艺术形象的塑造。一则汉水神女的故事流传广;二则在流传过程中其形象被不断丰富,有挖掘空间。汉水女神是中国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江河之神,她“辩口丽辞,巧善歌笑”。因而,汉水女神不仅出现在《诗经》、《楚辞》文化系统之中,也存在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祭祀文化系统之中,存在于民族文化的灵魂深处,得到了历代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的共同爱戴。 汉水神女的故事流传至今,已近三千年,其间在文人的创作中进行了不断的加工、改造、丰富。见诸记载的汉水女神故事,有两个版本:其一是被郑交甫挑逗而解佩的汉之游女,见于齐、鲁、韩三家诗传,是用来解释《诗经·周南·汉广》诗中“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的。后来被汉代的刘向收进《列仙传》:“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中当心。趣去数十步不见。”其二是与周昭王南巡,溺死于汉水史事有关。周昭王的两位侍女,“夹拥王身,同溺于水”,化为神女。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二女无辜而死,深得荆楚人民的同情。 “二南”诗的产生之地,后来皆为楚国所有,所以“二南”之诗又被称作楚辞之源。屈原流放汉北,其地正在襄阳附近。在长达九年的流放中,他创作了包括《湘君》、《湘夫人》在内的大量诗篇,,而“湘夫人”则正是“汉水女神”。湘君、湘夫人成为一对配偶神,是屈原对“湘水女神”、“汉水女神”故事的再创造。在《楚辞·九歌》中,屈原改“湘水女神”为湘君,改“汉水女神”为湘夫人,使他们成为配偶神。 秦汉以后,很多文人都从不同角度吟咏汉水神女,其形象便日渐丰满起来。王粲、孟浩然、王适、李孟阳等写神女的容止光辉,美丽娇好;欧阳修、苏东坡、邹浩等从教化的角度写游女的高洁华贵;张九龄用来表达知音难觅之意;鲍照、襄阳妓、袁奂等则从“不可求思”的角度写离别的愁苦。 今天,如果将“汉水游女”搬上汉剧舞台,可以糅合周昭王南巡以及屈原的《湘君》《湘夫人》的情节,再从后世文人对汉水女神的再创造中汲取一些因素,从中提取和平、和谐、爱情等文化元素来进行“汉水女神”形象的刻画。 汉水文化源远流长,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诗经》是汉水文化的载体之一,挖掘《诗经》中的汉水文化元素,形成以汉水文化为体,以由此衍生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所形成的人文环境、人文景观、人文精神为用的宣传推介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借势《诗经》打造安康的旅游文化情景剧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如果在汉水流域打造旅游文化实景剧,可以将汉水神女作为形象载体,将《诗经》中《周南·汉广》、《周南·关雎》,以及《楚辞》中的《湘夫人》等作品的元素植入实景剧中,突出生活的和谐安宁、爱情的生死不渝等主题。在剧情的设置上结合汉水神女的形象、汉水流域民歌盛行等要素,注入诸如山水、人文景观、民歌等安康旅游文化信息。 网络编辑:杜思颖 素材来源:宣传部 责任编辑:樊仁杰山雨 赞赏 |